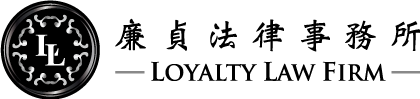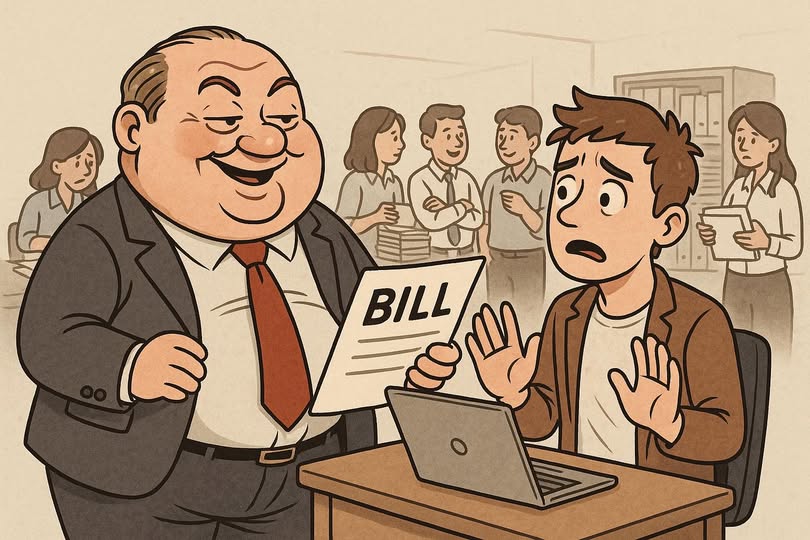最近美國與台灣分別針對新科技與著作權,做出不同結果的判決。
一邊是美國法院,針對AI訓練涉及著作權的案件,做出了對科技公司有利的判決。
另一邊,在我們台灣,知名法律科技公司Lawsnote的創辦人,因為著作權侵害被重判四年,還得賠償上億元!
這截然不同的結果,讓我們忍不住感嘆:「台灣法院對創業者會不會太嚴苛了點?」但別急著下定論,先來了解這兩起案件的本質差異!
▌Lawsnote vs. 法源:一場新舊世代的法律資訊大戰
把目光轉回台灣。Lawsnote成立於2016年,目標是打造一個「法律界的Google」。想像一下,一個能讓你輕鬆搜尋法律條文、判決書的現代化平台。
Lawsnote要挑戰的,是台灣法律資訊界的老牌巨頭「法源資訊」。法源從1986年就開始為政府機關維護法學資料庫,資歷深厚 。但在Lawsnote出現之前,法源的網站介面說實話,真的有點「復古」:你只能用最基本的關鍵字和案號查詢,而且必須「一字不差」才能找到判決。不小心用同義字?抱歉,查不到。想用律師或法官的名字找判決?那更是不可能的事。
Lawsnote看到了這個痛點,他們想用創新技術來解決這些問題。但要真正挑戰法源的市場地位,Lawsnote必須面對一個巨大的「護城河」:那就是法源經年累月建立起來的「資料庫完整度」 。
想想看,如果你要找法律資料,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資料要齊全。搜尋功能再花俏、介面再美觀,如果資料不完整,用戶還是會選擇資料最齊全的法源。
▌Lawsnote的「大膽」決定:爬蟲爭議浮上檯面
為了在最短時間內補足資料庫的不足,Lawsnote的創辦人做了一個「大膽」的決定:他們私下利用「爬蟲軟體技術」,大量爬取並儲存了法源網站上的法學資料內容 。透過這種方式,Lawsnote快速建立起與法源質量相當的資料庫,並開始逐步蠶食法學資料搜尋市場。
針對爬蟲軟體的使用,法院的判決明確指出:Lawsnote的行為被認定為「剽竊他人著作權」並「用於營利」,情節「重大」且「惡性重大」 。
▌美國法院 Kadrey v. Meta 案,與 Bartz v. Anthropic案
無獨有偶,美國科技公司為了訓練AI模型,也利用爬蟲軟體蒐集各種盜版著作,著作人憤而提告侵害著作權。
Kadrey v. Meta 案中,法院對於著作人提出的關於AI模型會重製著作片段,及其著作市場會遭到稀釋等論點提出質疑,認為著作人未能提出相關證據,進而駁回著作人的主張。
Bartz v. Anthropic案中,法院甚至認定AI系統從數千部書面作品中提取資訊以生成自身文本的過程,符合美國著作權法下的「合理使用」原則,因為其具有「典型轉化性」 ,也駁回著作人的主張。
▌為什麼結果差這麼多?關鍵差異
為什麼台灣Lawsnote案判這麼重,而美國AI訓練案卻對科技公司有利?這兩者之間,存在著幾個關鍵的本質差異:
差異一:內容「轉化」程度
在美國法院處理的AI訓練案件中(例如Meta的Llama模型),核心爭議點是AI模型使用受著作權保護的內容進行訓練後,所「生成」的內容與原始作品是否「本質不同」,具有一定程度的「轉化性」?法院認為,AI的輸出並非原始作品的直接複製或替代品,因此對原著作的市場稀釋程度較難證明 。
但Lawsnote的案件則完全不同!Lawsnote是直接提供「相同或類似」於法源的法律搜尋服務 。這對法源來說,就是赤裸裸的「市場稀釋」,因為Lawsnote直接提供了競爭產品,搶走了法源的用戶。
差異二:著作權「原創性」爭議
在Lawsnote案件中,Lawsnote曾主張法源對於法條、解釋函令這類資料的「編輯」是否真如法源所宣稱的具有「原創性」,這點在法律上仍有爭議 。畢竟法條、解釋函令本身是公開的,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;以此進行「編輯」,究竟要到什麼程度?才達到著作權法的「原創性」要求,值得深入討論。
在美國法院處理的AI訓練判決中,Meta和Anthropic所使用的訓練資料,實實在在涉及的是各種具有「原創性」的文學著作(例如小說、詩歌等)。美國法院前述兩個案件,僅在處理AI系統生成的成果是否構成著作權侵害爭議。至於Meta和Anthropic涉及的「非法從盜版網站獲取這些著作」行為本身,尚需面臨審判。
▌給創業者的啟示:AI時代的著作權新挑戰
Lawsnote的創業故事,不禁讓我們思考:如果Lawsnote的創辦人當年沒有急著創業,而是等到今日,利用生成式AI技術來提供「轉化」後的法律服務,判決結果是否還會這麼一面倒?
其次,法學資料理應由政府以更友善、便利的方式公開給民眾分享,屬於公共資源的一部分,卻因結構性因素而長年遭到維護承包商「法源」所把控,讓新創公司無法透過正常管道取得,這樣是否也是一種限制競爭行為?
令人感慨的是,AI技術轉化後的成果,對市場的破壞力可能遠大於以往技術;但因為根本性地改變成果本質,涉及很大程度的「轉化」利用,著作人反而更難舉證證明對原有著作市場的稀釋效果,就如同美國近年的AI訓練著作權侵害判決一樣,也更難獲得法律上的保障。
在數位時代,特別是AI快速發展的今天,如何在創新與法律之間找到平衡點,將是未來最大的挑戰。